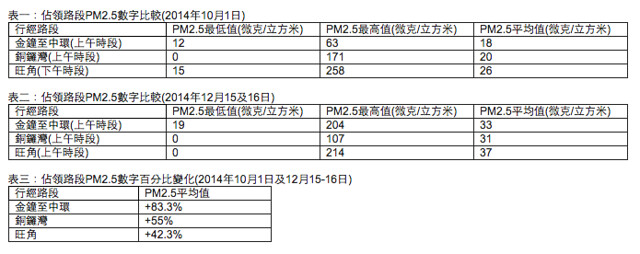警方雖然已經收起催淚彈及警棍,但警方濫權仍未停止。連日來的旺角「鳩嗚」,警方多次採取包圍行動,選擇性拘捕未成年鳩嗚「團友」。青少年不論成年或者未成年,均擁有參與集會的權利,警方此舉或已違反《聯合國人權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
選擇性拘14名未成年鳩嗚青年
警方在12月13日及14日兩天針對鳩嗚的行動中, 針對未成年人士作拘捕行動,一共拘捕了14人,當中7人於星期六凌晨被拘捕。星期日行動中拘捕的20人,也有7名年齡介乎13到15歲的未成年人士。警方指被捕者涉嫌干犯包括「參與未經批准非法集結」及「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等罪名。
沈偉男:沒法例禁止青少年晚上逛街
警方在打擊「鳩嗚」時,採取先設封鎖線再檢查身份證,然後才決定把誰帶回警署,民權觀察者成員沈偉男認為警察拘捕涉及選擇性執法。警方稱把未成年青年「帶返警署」的做法,是為了聯絡其家長接回,以確保他們安全,但沈偉男認為警察是以保護未成年人士為名,濫權為實。沈偉男指出,目前根本沒有法例禁止未成年人在晚上逛街,這行為不應被預設為不正常及違法,警察的做法或已違反《聯合國人權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侵犯了青年的「和平集會參與權」及當捲進法律衝突時的「受保護權」。
國際公約保護青少年集會及表達自由
攝:獨媒記者 Gundam
(獨媒特約報導)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在「失蹤」近一個月後,昨日(12月16日)親自主持記者會,他指自9月28日佔領行動至今共有955人被捕,警方會在3個月內完成調查,包括將其他主導者緝拿歸案,大有秋後算賬之意。除了所謂的「主事者」外,未成年少年亦是警方針對的目標。
在900多名被捕者當中,不少是未成年的示威者及佔中支持者。民權觀察者成員沈偉男指,雖然被捕人士享有法津賦予的權利,但即使是成年人也不太掌握當中的細節,他擔心未成年的青少年會在受嚇的情況下,向警方提供對自己不利的資料。
因參與遊行示威三度被捕,今年就讀中三、年僅14歲的學生組織「學生覺醒」召集人張浚豪,在今年7月2日亦曾參與預演佔中,是511名被捕者當中最年輕的一位留守遮打道的行動者。在人大831落閘後,他和其他北區學生成立「中學生政改關注組」,集中在北區的學校宣傳早前的學界罷課行動,及後再成立學生組織「學生覺醒」。在雨傘運動的兩次被捕過程,其權利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
學生覺醒召集人疑遭警點相拘捕
(獨媒特約報導)12月15日,立法會示威區內的佔領人士因應立法會秘書處的清場行動而撤出示威區,文化界監察暴力行動組成員、音樂人周博賢亦到場支持佔領者,並協助物資撤離。周博賢接受獨媒記者的訪問,談及對香港政制改革運動未來走向的展望。
現行監督警權機制無效
周博賢認為,運動現時最迫切要做的事是追究警方在過去兩個多月以來的濫用暴力情況,以及在「鳩嗚」行動中,濫權驅散群眾的問題。他指,現時警方執法為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事後就向肇事者說有任何不滿就向投訴警察課投訴,但其實投訴課甚至監警會的實效都很小,投訴個案與成功檢控的數字嚴重不成比例,根本無法監察警權。他認為,大家必須迫令政府成立更有效監督警權的機構。而文化監暴與獨媒最近亦成立了「雨傘警暴資料庫」,收集因警方濫權濫暴受傷的個案,不排除將來會就該類問題進行集體訴訟。
「無大台」變成運動弱點
餘下的佔領者現時僅佔據添美道行人路,在英國領事館對出亦有小規模佔領,周博賢認為,運動往後必須轉型,因為佔領行動在金錢上和生活上的成本都太大。「例如最近的鳩嗚行動,相對而言是本少利大」,他認為大家應該進行各類型的不合作運動,在各方面全面與香港政府抗衡。
當日早上筆者才跟記者說要坐在佔領了六十多日的帳篷等待警察,怎料食完飯,不能返回佔領區。思前想後,決定去自首。
我係由10月第2個星期四開始佔領的。
好記得,我當日食緊飯;林鄭喺TVB直播以一副官威話「對話不能有前設,不合作運動動搖對話基礎,明天不可能有建設性對話,因此決定擱置與學聯對話」,我當時感到好嬲好嬲、感到有種被政府當面侮辱了的感覺(見注1)。我決定響應黃之鋒前一日講「一人一帳篷」嘅口號,馬上由衣櫃執左一袋一星期嘅衫,直出油麻地買左個二百蚊國產帳篷,然後,在金鐘夏慤道開始左六十幾日的佔領。
往後一切,如夢。
我會記得市民說的每句加油、我會記得夏慤村村民親切的面孔、我會記得洗手間乜都有的奇觀、我會記得村中處處藝術擺設的美態、我會記得康文署體育館花灑的水溫、我會記得熱心太太送來鏞記燒鵝飯和雞湯的感動、我會記得被幾個黑社會大漢推撞時的無懼、我會記得清金鐘道那早上在警方防線和警方對話不成功後聲嘶力竭流下的淚、我會記得一大班人來話要拆大台時感到的無奈、也會記得最後一晚,廿幾個同系嘅同學整晚喝酒聊天到清晨......
在彌敦道被通車,旺角人群被強制暴力清場後,香港誕生了一種新型的群體活動。它無定時,無定向,無處不在。它極具香港特色,本是歡天喜地,卻總憤怒收場。這位抗命界新寵,名叫「鳩嗚」。
在香港人「心知肚明」之際,卻總還是會驚訝,為何警方會對如此無害,甚至有助經濟(好多人真係去買野咖喂)的活動,如此懼怕,如此憎恨,以致小事化大,全副武裝去打壓全無衝擊之心的鳩嗚隊伍。
行動的必要
回觀928一役,為何警察執意對示威者進行暴力驅散?真的只是做錯決定這樣簡單?依我所見,引致警方作出如此決策的動機,不是「這群人在犯法」如斯膚淺的理據,這只是他們的藉詞之一。請不必把那套制服過份正義化,他們想要的不是以拘捕來懲罰所有的違法者。如此決策的主要目的,不是避免一兩次的暴力衝突,而是維持整體上的穩定和治安;警方最執著的,並非活動實際上是否和平安全,是否違法,而是對於維持治安和穩定的Risk(危機)和Threat(風險)。
與不少同輩藝術家(較謙虛的喜歡叫藝術工作者)閒聊香港藝術生態時,談到香港藝術「被邊緣化」一事,大部分都表達出某種悲觀與消極。有的認為「係咁架啦」,本土藝術一向都處於邊緣地帶;有的為失衡的藝術生態抱不平的氣憤;有的表示享受在邊緣地帶創作的自由;有的擁抱學院派霸山頭小圈子桃花園的避世觀。
但一談到中(內地)日韓與東南亞的藝術品,在香港藝術市場中成為主流暢銷商品時,大家難免對仍處於邊緣地帶的本地藝術生態感到不滿與失望。藝術家一方面期待自己的藝術品能在主流藝術市場上展出與交易;另一方面又擔心主流藝術商品市場會牽制自己的創作。關於如何在創作自由與藝術市場之間找到平衡,又如何適當地作出識時務的妥協,這些掙扎讓一部分藝術家感到不安與疲倦,也導致某些藝術家選擇置身邊緣地帶的「假自由」。
但是香港藝術的邊緣化是怎樣造成的?
昔日的太古船塢,即是今日太古站附近。
「飛電師」是甚麼來的?每個字都懂讀懂寫,但合起來就不懂得解。當然,心水清的朋友看到後面寫着「xx師」,應該估到是一份職業來的。的確,飛電師是一份曾經是一份人人嚮往的職業。不過,一旦成為飛電師,其實是一個惡夢的開始。
故事要回到90年前,1925年左右的大古洋行主力經營海上貿易。太古主要有兩類貨船,一種叫「黑煙囪船」,專門行駛中國沿海各埠、長江流域一帶,至南太平洋、印度加爾各答的航綫;另一種叫「藍煙囪船」,是行駛澳洲墨爾本至新西蘭各埠。由於1925年中國及香港發生了「省港大罷工」,事後太古洋行認為獲得第一手情報極為重要。於是,他們下令所有「黑煙囪船」都要加裝「無綫電訊機」。所謂「飛電師」,就是在船上負責收發無綫電的工作人員。

太古船塢的船隻
圖:H15關注組成員(左二起)維怡、May姐、阿冼
(獨媒特約報導)城市規劃委員會於10月初開始審議新界東北大綱圖,城規會收到超過50000萬份意見書,其中90%反對,會議一直排至明年2月,但始乎誰也不認為城規會會真的否決大綱圖。城規會是否就是一個橡皮圖章?獨媒專訪數位城市規劃抗爭者,將以系列形式刊出。
當日的利東街,如今已經變成囍匯。當年有份參與保衛利東街行動、「H15關注組」成員維怡說:「一開始便對城規會沒期望。」雖然如此,他們確是走過在城規會據理力爭的路,除了在城規會反對市建局的重建方案,更透過無數的街坊會、家訪,在規劃師、建築師、測量師等的協助下,設計了第一個由下而上的「啞鈴方案」,自已規劃自己的社區。他們將方案提交城規會,結果自是遭否決。
差不多十年過去了,獨媒找來「H15關注組」成員回顧他們當年希望透過城規會制度改變政府規劃的過程與感受。十年過去,他們覺得只是在城規會制度內作用有限,「想不到竟然還有人玩城規會這個遊戲。」在市建局修訂後的利東街重建方案上馬後,當時上任不久,「好打得」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曾與關注組會面,林單刀直入的表示民間方案被否決,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換言之,政治高於規劃,亦絕對高於城規會。
攝:獨媒記者Gundam
金鐘清場,警隊好像突然換了另一副面孔,回到7月2日甚至更早之前的較文明狀態。於是林鄭月娥煞有介事地出來表揚這次清場行動,關注的是「高透明度」、「可以避免有人會對於我們警察的行動有一些無理的指控」。作為全港行政系統的首席官員,只關心警隊的名譽和形象,而非民眾的權利和安危,自是很教人有點失望;而對於理當如此的「高透明度」的刻意強調,反映的恐怕是過去兩三個月警方高層的決策和部分警員的行為,真的頗為黑暗。無論如何,「回歸透明」如果不僅是一次半次的公關妝扮,自然值得支持。不過,就算真的是迷途知返,也不能抹掉過去3個月出現的陰暗暴力,更不應忽略追究其發生的根源,以及帶來的各種深遠的負面影響。
暴力vs.權力
過去10多年,尤其是在曾偉雄和梁振英上任後,「暴力」成為了當代香港社會的一個關鍵詞。從WiseNews搜尋香港的媒體,「暴力」一詞在2001至2005年這5年間出現的頻率,近38,000次,2006至2010年則上升至近47,000次,到了曾偉雄上任後迄今的4年內(2011至2014年),進一步升至接近52,000次。然而,在本地的公共論述中,關注的往往是行為的形式,而非深究「暴力」的根本含意。顧名思義的結果,不僅無助釐清方向,甚至會轉移或遮蔽了真正的問題,讓我們難以從錯誤中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