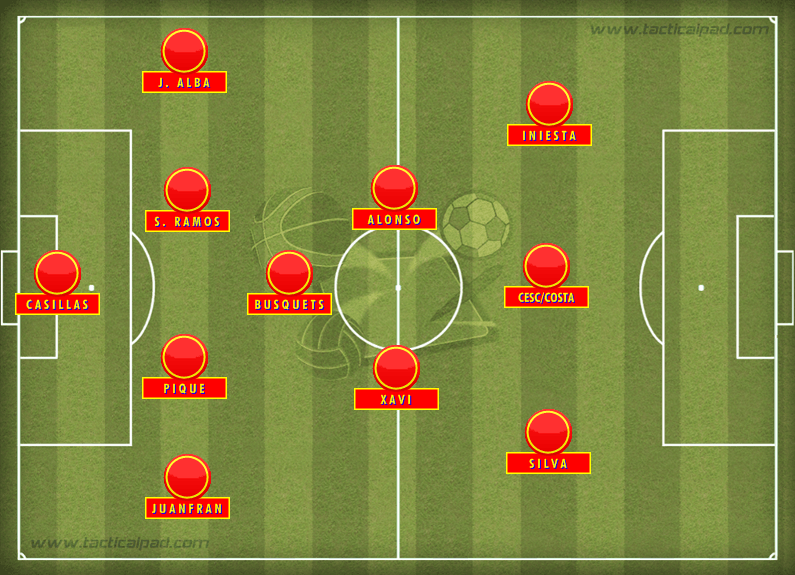編按:本文為中大學生會今年出版的《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 我們在北京…… 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其中一節,書本有十多位當年在北京親歷其境的中大學生的見證,中大學生會會於六四晚會當晚在維園設攤位出售本書。
「六四」前前後後的事
林亦子(八九民運期間為社會學系四年級學生、現職醫生)
(一)回想
快二十五年了,一直都不敢去碰「六四」的資料。零零散散的影像、文字總會碰到一些,但每年在特定時間展現在書店當眼之處的書籍,我一直迴避著。實在是太沉重了。一直知道自己的故事就在某一個角落的。
一直遺憾著、焦慮著、放心不下一段歷史被遺忘、曲解。不能再等了,腦子裏刻印著的記憶正在慢慢流失。
「八九六四」後,我急切地留下屠殺當晚的一切細節。這段經歷被錄過見證,也寫了下來。「六四」以前的故事呢?那麼多年一直沒有動筆。
這麼多年來,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晚會是每年盡可能參加的。即便是在外地不便參加,六四當天必會絕食24小時,並有一束小白菊花放在案頭。對於當年親歷這場運動的我,每年的節目就算多麼死板、口號又怎麼千篇一律,又有甚麼相呢?我們每一位學生畢生都背負了一個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