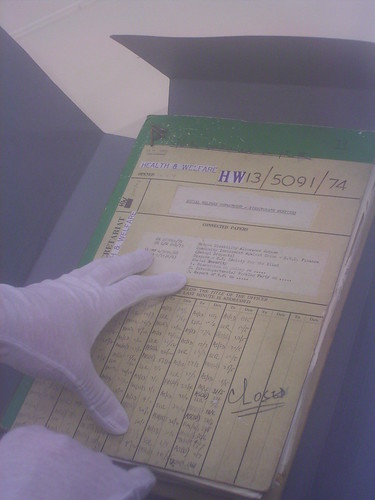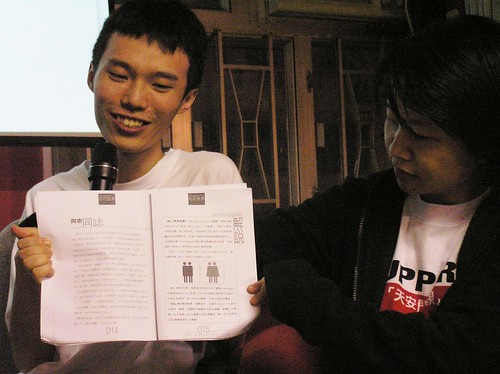
小弟弟開心地彈著琴,家姐向媽媽投訴說:「媽咪,弟弟侵犯我既版權呀!」
媽媽勸導弟弟說:「你咁樣做係唔啱架……」
這個政府宣傳片,相信大家印象深刻:小弟弟快快樂樂的彈奏,被姐姐保護版權的意識打斷了,再由媽媽的教誨作結。
版權 (Copyright) 本來的意思是作者賦予其他人複製流通作品的權利/協議,right to copy。可是,我們現在對版權的理解,卻變成一種限制流通的權力:「版權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保留該作品的所有權利。
當姐姐堅持自己的作品是「版權所有」,弟弟不能隨意彈奏姐姐的曲調,亦不能修改或延續該創作。姐姐也許保護了自己的版權,但她大概不會得到弟弟的尊重和欣賞,更窒礙了弟弟培養藝術和創作細胞。
保護版權≠尊重版權≠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