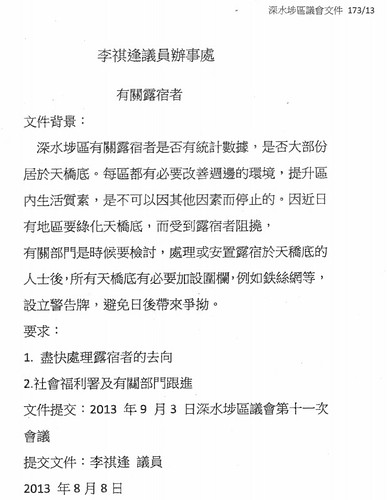環諮會昨天討論新界東北發展環評報告時,主要集中討論一條魚、一個鷺鳥林、土壤中含砷和補償種植等四個主要問題,即使有委員注關到發展會影響到現有的村民和農戶,向顧問提出一些例如復耕、搬遷等的問題,亦有委員指出環境影響評估在理論和書本上是會包括社會影響評估,這一切都被主席和在坐的所有委員認同這是現時香港環評制度所欠缺的一部份,這亦非現在環諮會所能討論或處理的問題,故此,我相信即使他們有不滿,仍為這個環評報告大開綠燈。
我細閱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499章),發現在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有以下的段落:
4.2 環評報告的目的及內容
4.2.1 任何規定的環評研究,其因項目而特定的研究目的及詳細範圍,須列載於署長所發出的研究概要內。典型的研究目的可包括下列:
筆者今夏在澳門一家獨立媒體當實習生,恰逢澳門特區第五屆立法會選舉,走訪選管會自然成為筆者其中一件要務。用一句話來形容選管會的工作,就是「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做盡」。
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宣傳期與香港不同,只有臨近投票日的兩個星期。這個做法理論上能保障財力、人力較弱的候選組別,但也有批評指兩個星期的宣傳期太短,「弱勢」候選組別難以接觸較多選民,選民也未必有足夠時間認識各候選組別。不過,更嚴重的問題,是「選管會有政策,(部分)候選組別有對策」,且選管會對種種「偷步」行為多採「隻眼開,隻眼閉」之態,令「偷步」甚至疑似賄選在澳門「經久不息」。
政府話,今日的年青人,20年後便是住在新界東北的新市鎮。我想,20年後香港人可能要去解放軍的軍事用地野餐了。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又「龜縮」寫blog,放言說要發展郊野公園。陳茂波說「發展郊野公園過往會被視為禁區、甚至禁忌,今天又是否完全不可碰、不可談呢?」政府強政勵治不理民意,假如執意要發展郊野公園的話,民間似乎也難以阻擋。20年後港人要找一片郊野平地野餐呼吸,剩下的可能只有真正的禁區、禁忌——軍事用地了。
抱歉,我不滿足於香港一直沒有單程證審批權的直觀解釋──即北京想控制香港,溝淡香港。還記得Minna Ho替我們解謎,解釋雙非能夠在香港有居留權,是因為讓包括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在港所生子女獲得居港權,鼓勵移民港人回流。Minna Ho引述李柱銘轉述魯平的話,指「魯平拍心口說中央會控制內地人來港」。
結果,在《基本法》制訂後到今天,至少有100萬名單程證移民及雙非有居留權。是否逼爆香港,並非本文的討論主題。本文嘗試在有限的文獻中尋找線索,解釋香港為何沒有審批權,這包括歷史和政治因素。現實,遠較我當初想的複雜。
暑假完結,師生回到校園,但關於教育的風波卻仍接踵而來。先有報導指科目滲入洗腦內容,再有立法會議員指通識科內容不應佔太多和政治有關的課題,提出由必修科改為選修科;甚至建議廢除科目。更不要說林老師事件的餘波未了,除了在過去個多月來受到文革式批鬥外,亦被迫放下教鞭休息一個月;她更在前幾日更接到刀片信恐嚇。這一切都說明政權開始深諳教育的「重要性」,遂要對教育進行內外的整頓,而且將來情況亦只會有增無減。
教育在社會學中的功能既有顯性功能,也有其隱性功能,教育最基本的顯性功能就是知識的傳遞。隱性功能就是其社會化及傳播文化,當中透過學習的過程令學生在社會及其所屬團體中履行他們在社會上的角色。簡而言之,就是在學校及學習的過程中找到歸屬感及個人的未來發展取向。一直以來都說十年文革之所以可怕,就是因為挾持及控制了人民的思維及意識形態;去年擬開科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就有異曲同工之處。
當局之所以看中通識科,原因呼之欲出,就是因為該科強調批評性思考,並包含民主和人權等普世價值;比只紀錄官方和政府不是的中國歷史科「恐怖」上百倍。如上曾言,殺掉或令其轉作選修正是要令學生不再社會化,回到只是課本上的內容,毋須再去了解政治和社會每日所發生的事,更遑論要有批評性思考。不知道便不批評,不批評便不抗爭。那時候,沒有反對聲音,自然人人是順民。
亞視浪費大氣電波已經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通訊事務管理局本來要做的就是收回亞視牌照,再發給有心經營者。現在就算迫令亞視辭退盛品儒,也不能令亞視變回「正常的」電視台,只要王征起用「醜怪版盛品儒」雷競斌,根本不會轉好,甚至只會變得更壞,而類似雷競斌這種代用品多着呢。
罰款一百萬也是無濟於事,據 Tony Choi 《洗紅錢》一文推斷,「入主亞洲電視四年的盛家,據稱已投入了十六億元,觀乎亞洲電視近年業務,除了新聞部之外,就只得賽馬節目有人做事,完全無自家製作的劇集,其他綜合節目亦極少,多數是一些左派人士的清談節目,最離譜的是連三十年前的《方太與你》及《開枱》都夠膽找出來重播,基本上真的不費一分一毫,究竟四年如何蝕十六億呢?」「這間電視台基本上是零收視兼完全無廣告,但竟然還有800個員工,很多中共喉舌統戰機構的退休員工來到了亞視工作(按:很可能用他們的銀行戶口以出糧的方式協助洗錢),而亞視就直接向維穩辦申請經費,以他們的支出每年不出一億,虛報四年用了十六億,即是說他們這四年最少吞了十二三億,有甚麼生意好得過『洗紅錢』呢?」(引文略有改動)如果蔡先生之推斷沒錯,區區罰款一百萬,又算甚麼呢?
港台《海底交易》是近期佳作。最近一集講述海豚保育,其中一個登場人物,以前從事捕殺海豚,如今改為當海豚導賞員。他的一番話,令我感觸良多。
這位石井泉先生,大半生以捕殺海豚為生。一次,當他如常捕獵,正如舉刀割喉時,竟看到海豚流淚。之後,石井泉放下屠刀,改當海豚導賞員,以贖往昔之罪。但他承認,當導賞員的收入大減;許多捕獵者如停止捕獵,生活無以為繼。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為保育海豚和鯨魚抗爭,這是很容易的事。但更重要的是支持和幫忙轉行帶導賞團的漁民,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現在放棄,便證明了漁民不能靠導賞團維持生計。我現在的心裡也搖擺不定。」
石井泉如是說。生計,是最現實的問題。
套用電影《狂舞派》的宣傳口號:「為了海豚,你可以去到幾盡﹖」我想大部分人想到的,首先是「捐錢」,然後是「行動」,包括(以下按困難程序排序)口講、不去海洋公園、參加示威、組織示威……我想,要去到好盡好盡,才會放棄自己的生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