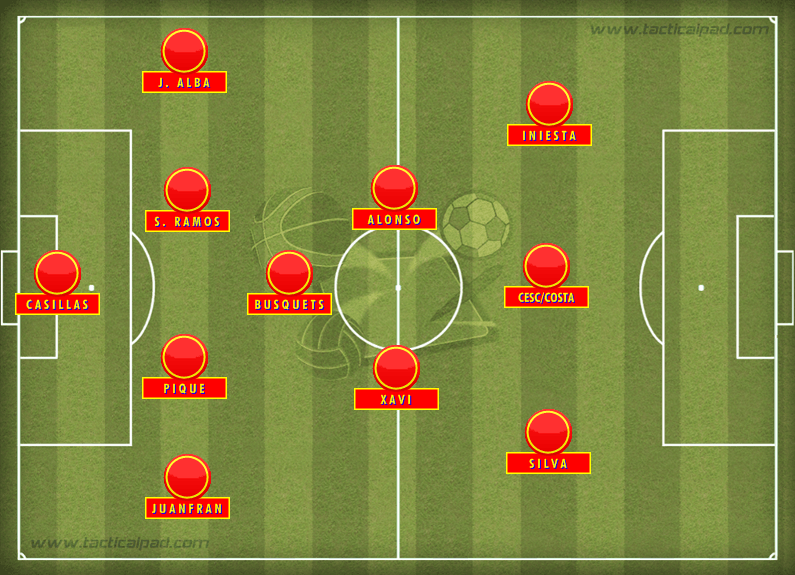同樣是在自由廣場,在228當天這裡有活動,64這一天也有悼念的晚會,兩件事情的本質都一樣,當權者屠殺人民,歷史記下了這筆帳。
出席的人數據聞有3000,對照香港那動輒過萬人的晚會,這個數字彷彿不是甚麼,但每一個個體的出席,都代表了一份意義,與人數無關。
「路過天安門,人人坦克人」簡陋的大台,由吾爾開希作開始的致詞,然而教我記住的卻是另一個當年的參與者童屹的致詞,她把內容都放了在前陣子被捕的浦志強律師身上,她的好朋友,讀起他的文章時更一度飲泣。
到了最後一部分,以台灣組織的發言為主,印象深刻的是陳為廷,雖然他的發言一如以往般長氣及跳躍,但卻提出了一段我不知道的過去,說起1989年的台灣,在六四屠殺發生以後,自由廣場上曾經有著數萬人的集會,那是國民黨以「自由中國」來攻訐「紅色中國」的年代,而在六四發生前的兩個月,才發生了鄭南榕自焚事件。
台灣爭取民主的道路走來不易,近年更彷彿是華人社會裡的一盞燈,當陳破口大罵「去他媽的甚麼民主燈塔」來指向現今台灣民主的倒退,威權體制的陰霾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他也談到了台商這些年來在對岸進行的政治獻媚與剝削。燈塔的重燃依靠的是每一個人的思考及參與,中國、香港、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