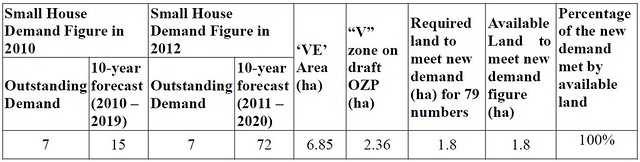二十五年,的確是人生、一個機構、又或一件事件紀念的里程碑;銀禧、金禧、鑽禧、百周年的標誌,之所以為人所重視,就是二十五年作為倍數,一代又一代地層遞上去。或許今天筆者剛滿二十五歲,是個紀錄的機會。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寫過:『對我們所有人而言,在歷史和記憶之間都有一塊不很明確的過渡區…對個人來說,這塊過渡區係由家庭傳統,一直到嬰兒時代結束,由最老的家解說最早的一幀照片,到(自己的)公共和私人命運互相決定為止。』
碰巧,由長輩對我講述三年零八個月,再到自己懂事並對公共生活產生印象之前的過渡期,剛好有大約五十年分屬兩代香港人的時段。而且,還應強調這是第一次屬於『香港人』的時段。第一段,是祖執輩逃避日軍或內戰戰火南來、石硤尾大火流離失所的年代,他們也就在此定居了;第二段,是父母執輩成長的故事,是香港經濟起飛、本土文化興起的年代,不只在地域上,連生活方式也自成香港人一格。
在『不變』和『轉變』之間
接下來八十年代香港社會在預備一次轉變。八四年簽訂聯合聲明,前途在不明朗的氣氛下確定,香港在一兩代中積累經驗和生活方式成為『五十年不變』的對象,但『不變』口號回應着的卻是『轉變』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