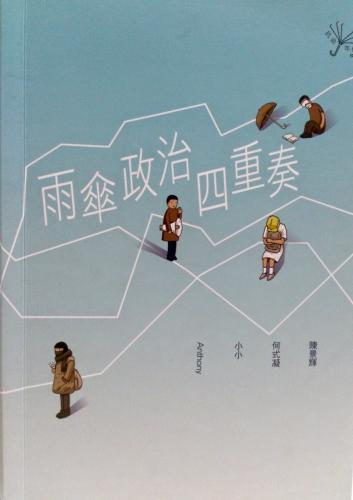
1
學聯升級前夕,旺角已遭清場,化成流動「鳩嗚團」。金鐘佔領區,不無膠著和疲倦,但也像垂死的野獸,侍機反噬。
宣布升級,我和身邊朋友的心情確實有些複雜。大原則當然是支持學生,並把握這次反擊的最後機會。但同時間,我們也不知升級確切意指什麼,是指佔領金鐘以外的地方?佔領政府建築物?但以什麼方法及如何分工?外間並不知道。
加上,網絡一直有人鼓吹暴力抗爭,派系紛爭也激烈,到時候雙方要不要劃界呢?如何區分?也不知道。
那天黃昏,我得先去「九龍城書節」做評論嘉賓,跟長毛、吳靄儀對談民主運動的過去和未來,之後便跟部分書節的友人,匆匆趕去金鐘,我隱約感受到大家的未知和緊張。
2
我們到了現場,台上同學正好呼籲群眾去包圍特首辦。我心急,自己即戴上防護眼罩,隨人流而去,友人卻停了下來,說要先「煲飛煙」,就這樣我們失散了。
上到添馬公園,當時龍和道的防線還沒突破。衝突點至少有兩三個,都在防線跟警察推衝。公園沒有大會,群眾得自己選擇加入不同的衝突點。同時,四方八面傳來要求雨傘、眼罩之類的支援叫喊,聲嘶力竭,很觸動神經。不少群眾則分佈在草地的不同角落,悄悄聲援。
未幾,龍和道近海傍的一條防線遭成功突破,於是人群湧進馬路,我亦本能地湧前,跨越一道圍欄,瞬間,已踏在行車線上。
突然,倒是反高潮,身旁一把聲音傳來:「死左膠,你係到做乜,收皮啦陳景輝!」這個人蒙面蒙及至頸,只剩下一雙眼睛,手指著我的鼻。
當時場面混亂又緊張,警察時刻企圖反攻,佔路未穩,一時間我不知如何回應。他身邊也有幾個蒙面同志,但似乎摸不著頭腦,問他在罵誰,有點茫然。
突然,失散的友人來電,問我位置在哪。我們幾人遂相約先在草地上重新集合。
為了要返回草地,我又跨過那道圍欄,這次朝相反方向。但沿路,聽見罵聲不斷,但今次主角不是我。是一些年輕人,有的拿著大聲公,有的沒有,罵草地群眾,指罵他們站著聲援:「仲記唔記得你們自己的初衷是什麼呀?仲站在草地幹什麼,好多人已經去了馬路!幾時先識醒,死到臨頭,你們卻只懂得和理非非!」
像首憤怨的樂曲,這段激進說教,全晚奏個不停,傳遍佔領區,疲勞轟炸那些沒湧上馬路的人。
我難過!心想,草地的群眾,本來就是在運動後期,最願意支持金鐘佔領的香港人。面對那個場面,他們沒有即場決定衝出馬路,可能是出於緊張猶疑、準備未夠、個人考慮,甚或現場太亂、看不見雙學代表、眼前所見違反預期等,諸如此類,但他們在這個晚上仍然選擇來到現場,就已經表明了願意跟雞蛋站在一起的心情。
但是,同路人的差距和差異,換來的不是諒解或想方設法的拉近,甚或互補,而是憤怨的咆哮。這就是所謂雨傘運動的「衝衝子模式」,下面將展現得更清楚。
3
很快,我跟失散友人重新會合。這時,龍和道另一條行車線(近特首辦),也成功搶佔。我們又跑了上前,瞬間我又站回那條馬路上。這次人更多,群眾分別佔據兩條行車線,但尚未填滿。
突然,又來咆哮。一些人不滿近海傍一邊行車線上的群眾(包括我)不貼近特首辦那邊的馬路,他們喝斥:「過來啦,站在那條馬路有什麼用,特首辦在這裡呀?!民主不是一朝一夕,醒未呀香港人,仲記唔記得自己的初衷是什麼?」
我原以為,這首憤怨的樂曲只會轟炸草地,沒想到,它也會在馬路奏起,再為兩條行車線上的人群,分別貼上「有否遺忘初衷」的標籤。
在此,我們墮進了一種勒索式的行動想像,每個人只能二擇其一:「要麼(再次)衝擊,要麼回家睡覺!」這,就是「衝衝子模式」。
4
友人跟我已經受不住這種氣氛,決定乘尾班地鐵離去。
不消一小時回到家,第一時間扭開電視。至今,我仍很記得那直播新聞畫面:特首辦外已排了多重防暴警察,此時前線一些群眾內部卻在發生衝突。
新聞主播報導說,一些主張衝擊的「衝衝子」,和現場的李卓人發生口角。部分人要求他領軍衝擊特首辦,並傳他工人帽、眼罩,並揶揄說「若願帶領就封他為偶像」。
同一時間,前線行動者劍拔弩張,已有零星衝擊(還記得新聞畫面有些晃動)。
心急的我對著電視機自言自語:「不要衝,一定衝不過!」
突然警方率先行動,一群藍衣人湧上馬路,狂毆示威者,棍如雨下,短短10多分鐘,人群如鳥獸散。
這夜的新聞影像,充滿嘶叫、暴力和痛楚。
後來翻查資料,發現李卓人那段小插曲,很有寓言味道,足以暴露我們自身的政治困局。那一刻,被人潮推了上前的李卓人,其實不願意再次衝擊,主張應當以佔路形式包圍特首辦,而最前排的衝衝子則堅持「行動升級就是衝進特首辦」。
當然,李卓人的想法換來的只是嘲笑。電視機前的我,感到深深的無力和悲哀。想起中學時的足球教練經常告誡說:一隊波,不能「有前無後打死罷就」,除了進攻,也要顧及防守和整體,否則一個閃失,一旦對方反擊,就甚麼都沒有了。事後孔明,如果我在場,我會建議大家在兩條龍和道都坐下來,是守,這樣子警察就不容易清場。
然而,這根本不會發生,因為衝擊之外的什麼建議都不可能被聽見,更何況是我建議?!讓我們重溫,所謂「衝衝子模式」,就是:「要麼向前衝,要麼回家睡覺!」。說穿了,這是一種要錢定要命的勒索,是以行動之名所施加的不自由狀態,我們都被禁止討論和思考在此之外其他「共同行動」的可能。
我們彷彿都捲入一個激進的怪圈,無休無止,哪怕你走在草地、馬路或已像李卓人般貼近特首辦,你仍會被譴責忘記了初衷,只因為你沒有再「向前衝」,即使有時再衝是自毀長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