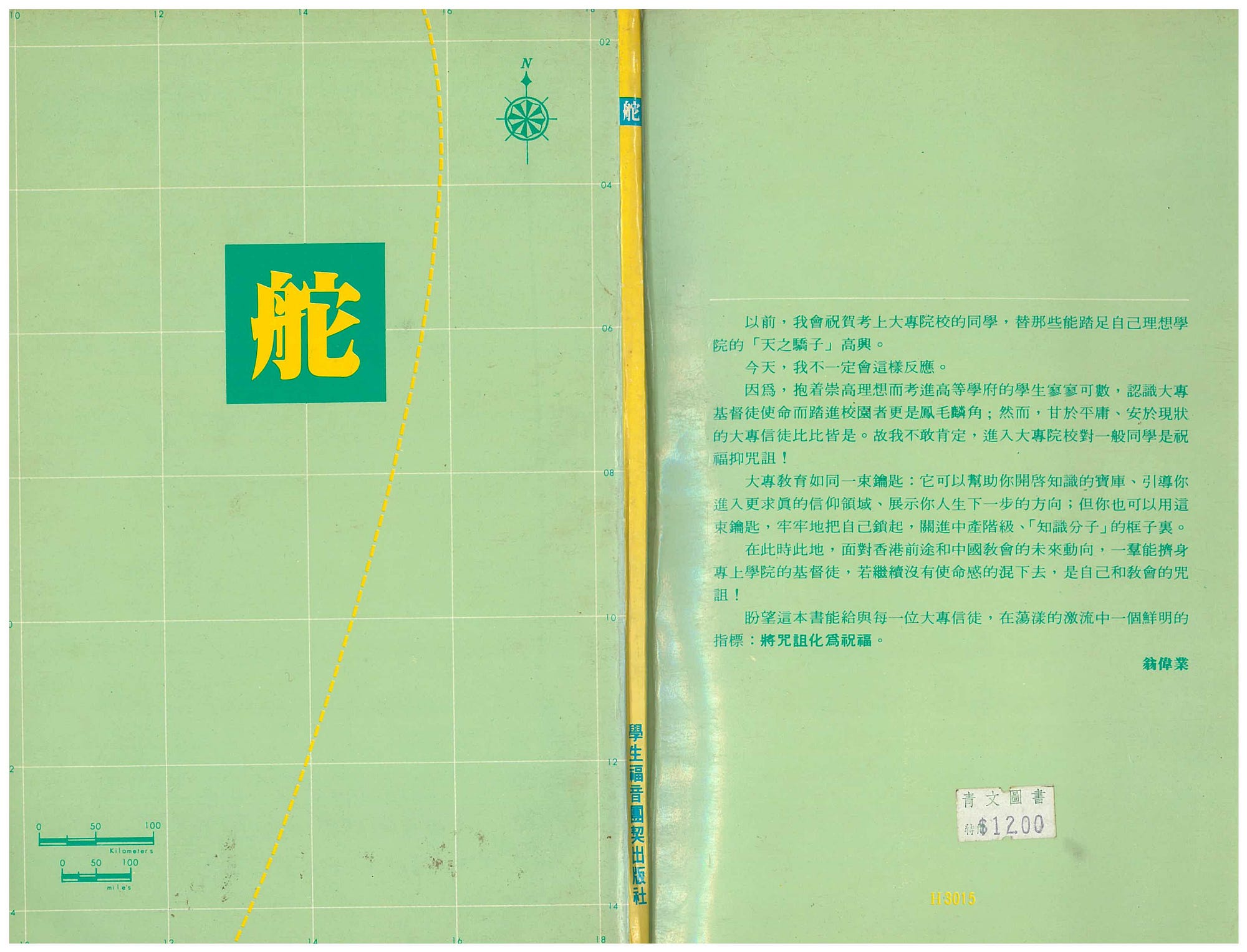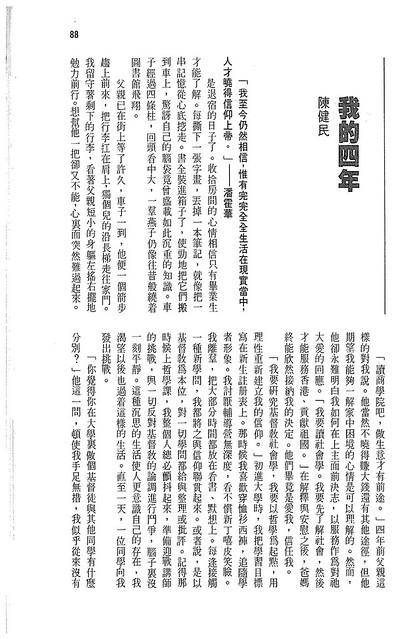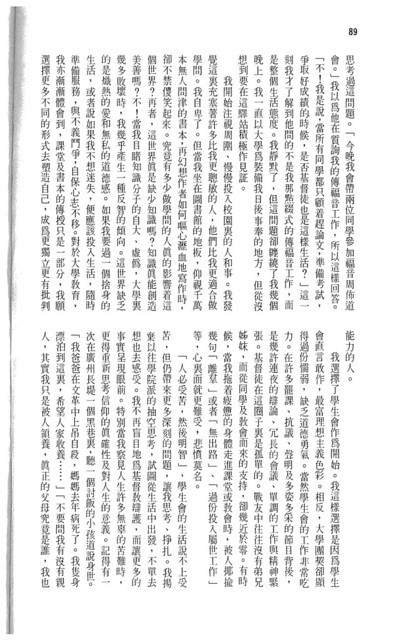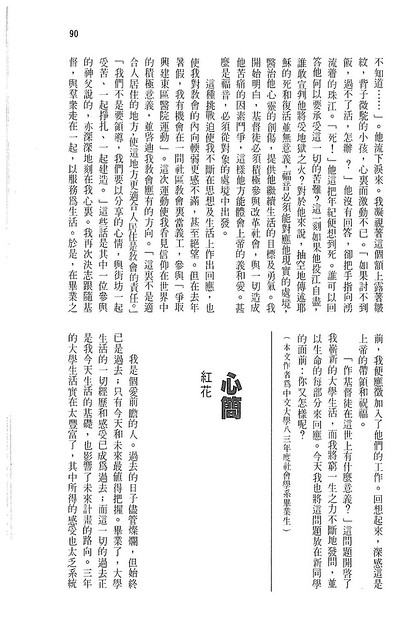陳健民兄在中大「最後一課」中自白:「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並剖白了他從中學到大學期間的信仰歷程。
關於他在大學時代的信仰之旅,他在1983年於中大社會系畢業時一篇文章〈我的四年〉,從第一身角度作了回顧。文首一開始,就引用了潘霍華在《獄中書簡》的話:「我至今仍然相信,惟有完完全全生活在現實當中,人才曉得信仰上帝」。
文中呈現了他的信仰歷程:初進大學時,他跟家人說:「我要讀社會學。我要先了解社會,然後才能服務香港,貢獻祖國」。他又在大學新生註冊表上寫上:「我要研究基督教社會學,我要以哲學為起點,用理性重新建立我的信仰。」後來,由於一位同學的問題(「你覺得你在大學裡做基督徒與其他同學有甚麼分別?」),醒悟到要信仰必須「投入生活」,而不只是「點綴式」,於是便開始參與學生會。
作為基督徒,在學生會的工作,令他經驗到很大的孤單。一方面,是學生會內活躍的基督徒很少,缺乏信仰相同的戰友;另方面,是他不能從弟兄姊妹中獲得認同及支持,更被教會視作「過份投入屬世工作」,令他感到難受。然而,參與學生會卻讓他「不再盲目地為基督教辯護」,特別是當他察見「人生許多無辜的苦難」,逼使他「重新思考信仰的真確性及對人生的意義」。他提及在廣州面對一位在街頭討飯,人生毫無盼望的小孩時,想到「抽空地傳述耶穌的死和復活並無意義,福音必須能對應他現實的處境,醫治他心靈的創傷,提供他繼續生活的目標及勇氣」。他明白到,「基督徒必須積極參與改革社會,與一切造成他苦痛的因素鬥爭,這樣他方能體會上帝的義和愛。甚麼是福音,必須從對象的處境中出發。」
這種反思,令他對教會的「內向輭弱」更感不滿,「甚至絕望」。但當他有機會在柴灣一社區教會當義工,並參與了爭取興建東區醫院運動(筆者按:他大學畢業時的功課,便是以統計數據來支持興建東區醫院),再令他「看見信仰在世界中的積極意義,並啟迪我教會應有的方向」。一位神父曾跟他說:「這裡不是適合人居住的地方,使這地方更適合人居住的是教會的責任」,「我們不是要領導,我們要以分享的心情,與街坊一起受苦,一起掙扎,一起建造」。於是,陳「再次決志跟隨基督,與群眾走在一起,以服務為生活」。大學畢業後,他更加入了有關社區的工作(筆者按:即循道衛理愛華村服務中心)。
陳健民在文末說:「作基督徒在這世上有甚麼意義」這問題,需要「窮一生之力不斷地發問,並以生命的每部分來回應。今天我也將這問題放在新同學的面前:你又怎樣?」
關於健民兄往後的信仰歷程,日後望有機會再作了解。不過,現在回看,他多年來對中國公民社會的關注與委身,對香港民主運動的付出及承擔,事實上已在他早年的反思與立志中見到端倪--「基督徒必須積極參與改革社會,與一切造成他苦痛的因素鬥爭,這樣他方能體會上帝的義和愛。甚麼是福音,必須從對象的處境中出發。」
健民兄在「最後一課」中說:「遙遙長路,有時真的覺得前路茫茫,燈有時會暗淡。暗夜裡,可以怎樣?我想只能看星。」
此時此地的香港基督徒,該如何面對「作基督徒在這世上有甚麼意義」這問題?端在於,我們所信仰的到底是甚麼?又如何實存地,在真實及苦難的處境中,以自己的生命去反省及實踐。我們所信的在當下有何意義?這確是一生的功課,特別在黑夜之中,感到迷失及灰心時,健民兄所指的「看星」,也許就身心安頓的價值及信仰,看著星,窺見這個世界以外的永恆,因而得著勇氣、力量,盼望黎明來到的那一天……
(後記:筆者於1983年9月入中大,那時健民兄剛好畢業。他文章最後問「新同學」的問題,卻沒有讓我這「新同學」注意。我在1984年始於大學決志,1986年2月15日才在灣仔青文購得此書。不知為何,當時並沒有細讀陳文,反倒是前陣子整理九七與香港基督教時,才赫然發現健民兄這篇文章。近日細讀他的「最後一課」,再想起此文,以此為記。)
參考:
陳健民:〈我的四年〉,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八三」迎新事務籌委會編:《舵》(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1983),頁88至90。